 联富配资
联富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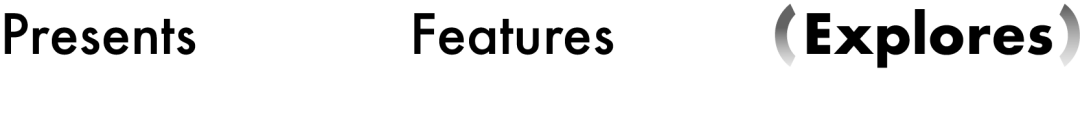

严明觉得,摄影师像一个刀客。一方面是因为快门,按下它的瞬间如手起刀落,“切下一刀,形成一帧画面,是拍摄过程的切片,也是人们观看世界的切片”。
另一方面是因为心软,两者都有一种行走江湖、不断体验和找寻的感觉:“见到苦难或劳作中的人、奋起同理心,不自觉地拿起相机记录眼前的一切,也是另一种‘拔刀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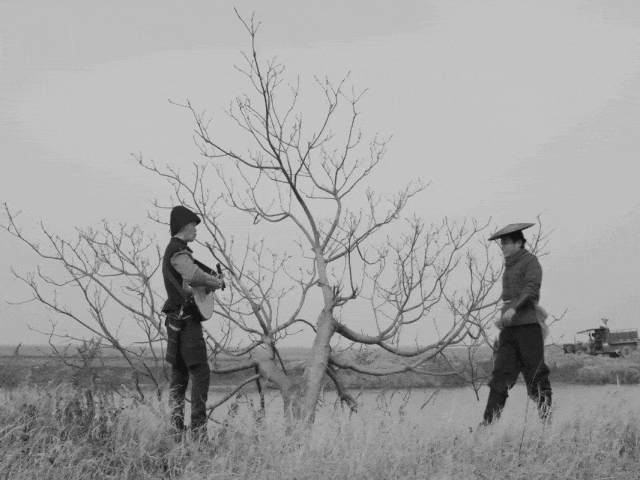
2010年辞去报社工作、成为自由摄影师后,严明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一张卧票,背上一个装满摄影器材和胶卷的大包,伴随着绿皮火车23小时的哐当声,前往他的第一站:重庆,一个有江湖气息的城市。
重庆有一个朝天门码头,它是两江交汇的三角地带,上半城和下半城的交汇处。有一段时间,严明沉迷拿起相机,拍下江水东去、往来过客;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在这里,人与环境的相处、人与人的相遇常有惊喜。我常想,如果最初到达的地点不是重庆,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的摄影之路会是怎样?也许还会再徘徊个两年。”
辞职的同一年,严明凭借《我的码头》获得法国才华摄影基金的摄影奖;2011年又凭《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一以贯之的方形构图、黑白胶片风格、镜头下的人文关怀和写意,让他成为读者口中的“诗人摄影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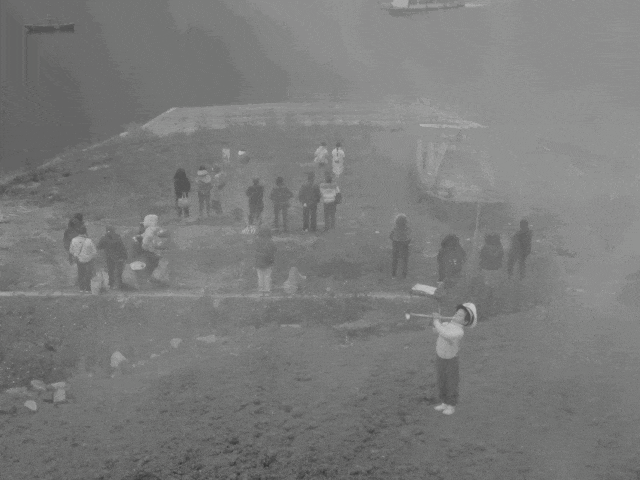
然而时间在前进。严明渐渐感受到,刀客或行走江湖不再“流行”,哪怕是最擅长耍大刀的关羽——有一年在老炉殿,严明远远看到殿内供奉着一尊关公像,走近却发现只是贴在墙上的户外广告喷绘画布,有的画像取材自网络游戏,由于图片原文件不够大,线条边缘还出现了锯齿;这几年,朝天门附近被高楼大厦占据,路上总是堵车,“要是现在还有年轻人标榜‘行走江湖’,我甚至想说大可不必。”
今年,严明的摄影随笔集《大国志》迎来10周年再版——导演何国政正在进行新人物系列影像创作,他从严明的照片和“刀客”形象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人物短片《单刀会》:时间、刀客、江湖,刀客穿行在充满水墨和东方感的黑白影像中,十年间的经典场景被复刻再现,一个时代的“刀光剑影”,也许是南柯一梦。

严明对于时代变化的伤感很早出现在《大国志》中,他用镜头记录经济发展的热潮下,传统人文环境的落寞、大国小民的日常,他感怀过去已经远去,未来还不清晰。NOWNESS和严明聊了聊天:十年甚至更早前思考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新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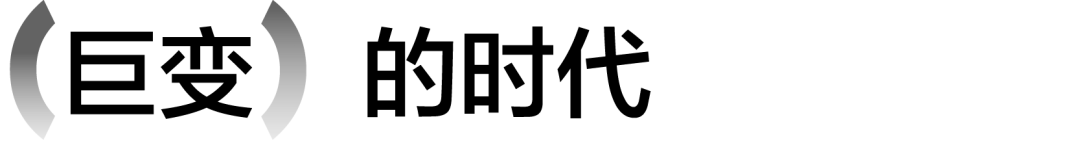
在入行摄影之前,严明做了十年的摇滚乐手,但不幸发现自己理念有误,且处于一个技术和资源相当匮乏的时代尾声,“在我之后一代的乐手,已经可以在网上轻松下载音视频教材、演唱会现场、大师访谈等,新人完全可以在两三年内走完我奔波10年的路”。
好在音乐上的失败成为前车之鉴,为日后入门摄影提供了经验——不迷恋设备、追逐技巧、模仿他人,而是表达。
 联富配资
联富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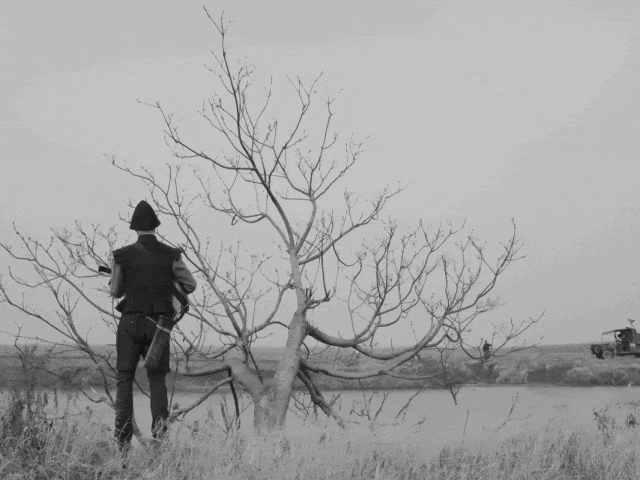
将近32岁时,他入职南方的报社,第一次摸到相机,很快从文字记者转行到摄影记者——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明天天跟着同事“扫街”、研究光圈和快门的设置,也在他人提醒下很快发现相机只是工具,越专注器材只能说明自己越不成熟。
严明至今还记得一位艺术家朋友对自己说的四个字,要有态度:光是痴迷设备、勤于练习还不行,要有对世界、对社会的个人看法,反映出来,投射出来。
这让他很早开始思考摄影的本质,“就像画画和写作,没有人只是对颜料和毛笔感兴趣,你最终还是要写文章,写诗歌。技术只是手段,表达才是根本。”

然爱你,《昨天堂》
基于这一理念,日常工作开始与理想背道而驰。某种程度上,他觉得新闻摄影是在重复某一种模版、完成某一个命题作文:过年拍春运,拍火车站;六一拍儿童,拍幼儿园。尤其是在工作十年之后——在广州已经待了太久,严明想把自己的拍摄范围扩大到江河湖海、去往北方寻求更自由的体验。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2010年,严明辞职前往重庆。他在工作时就出差到过这里,后来在书里写道,这实在是一个太有江湖气、太过迷人的地方, “一阵江轮汽笛的呜鸣,惊醒我汗湿的梦。穿过融混着柴油与江水腥气的船舷,挤过人群来到船头甲板边上,江水尽头浮现出影影绰绰的城市轮廓,层层叠叠的房子,像江上客轮的船舱依次层叠,完成从下半城的寻常世界向上半城的想象世界的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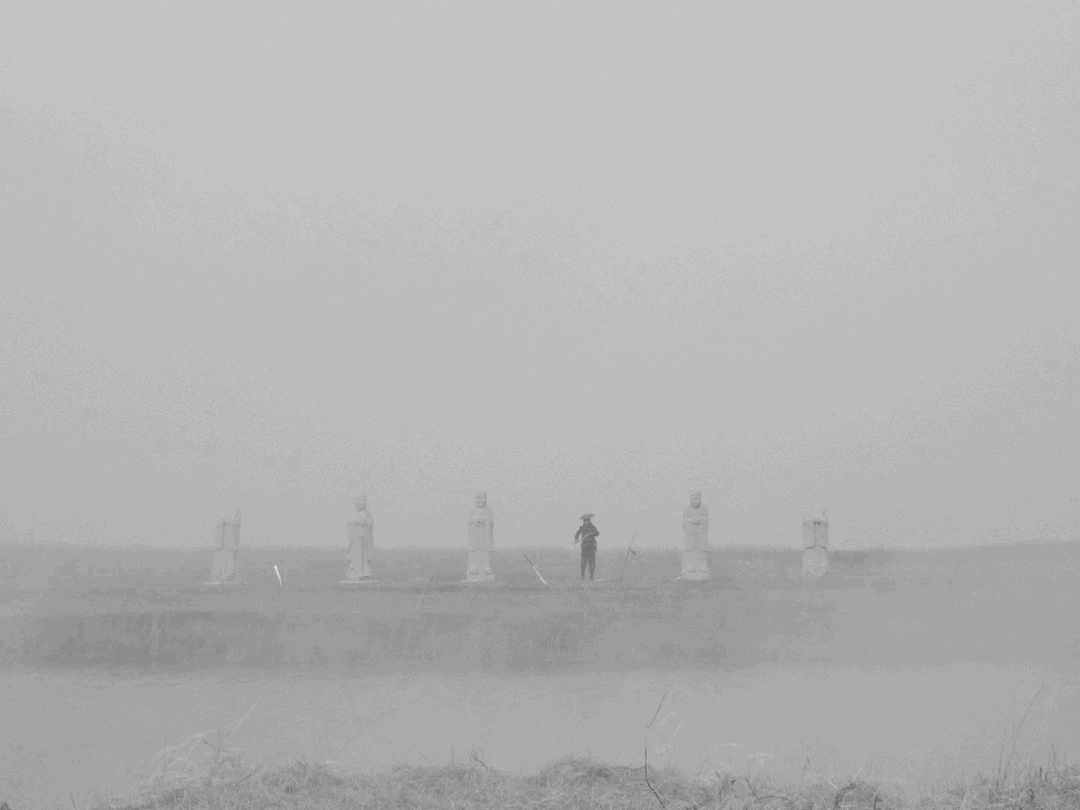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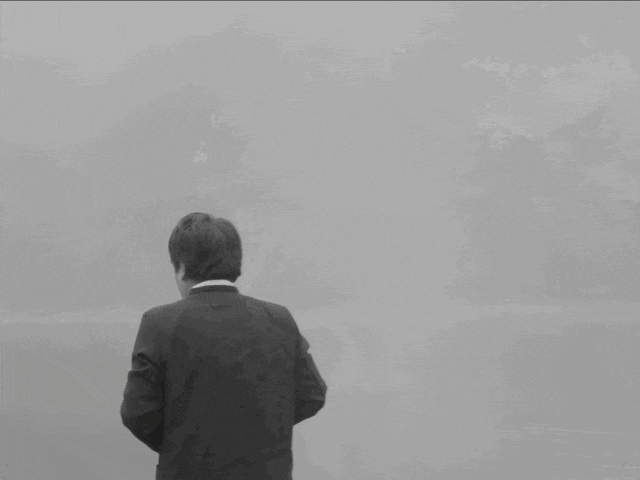
在重庆,严明认识了当时同为摄影记者的铁蛋,在这位“袍哥”的带领下认识了很多好友,两人站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探讨“摄影的担当与不担当”、“离得足够近还是离得不够远”、“拍照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等问题。
在这里,严明如饥似渴地开始了第一波创作。大多数时间,他拿着老式黑白胶片机出门,拍下那些被忽略或遗忘的人文景观:走进刚创建的重庆洋人街,拍充满奇幻的游乐场、下班的“米妮”和工作人员;站在朝天门码头的台阶上,拍拾级而下的贵妇;十多年来,他已经熟悉每一条从滨江路遛下原始江岸的小道,“难以想象,我可能去过100次重庆了”。
过去的报社经历也带来了一种经验:曾经的设备器材、采访条件、接触社会的人间冷暖,让他习得与人打交道的技能,“后来辞职去跑江湖的时候,遇到人、遇到事就会不那么害怕,也敢解决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严明对摄影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摄影师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强调关键的时机和位置;而严明则想到“决定性氛围”的重要性:一张好照片在信息要素之外,还应该有恰如其氛的整体情绪,比如宁静,比如凄清,在客观上叠加一种“代入感”。
重庆恰巧就是这样一个“出片”的城市,“世界和时代的变迁令人恍惚,这是正常的,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去对了地方联富配资,没有辜负那个巨变的时代。”

下班的米妮,《大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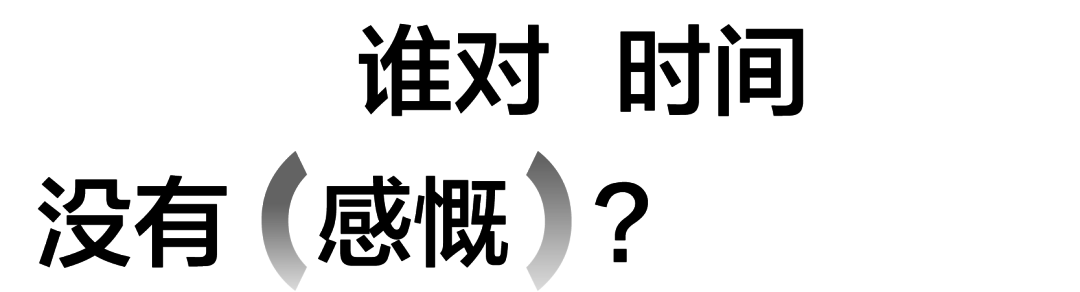
严明记得,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报道摄影的一个金句,而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抓起相机就往回跑”——不怕把拍摄对象拍小,只想把环境氛围拍大。
2010年,在《大国志》的推荐语中,编辑形容严明是一位“诗人摄影师”,这是一个他事先并不知情的宣传文案——但他的确觉得,如果自己的作品当中有诗意,是因为这是一个不缺乏诗意的国度:中国古代山水画很智慧地运用了“远”的力量,让观看有了视觉延伸,将观看转移至想象。
“我自己拍的作品,实际上也借鉴了我们古代山水画、古诗词审美里的东西。中国文化对于视觉的描摹、视觉情绪和意向的刻画已经炉火纯青,‘平沙落雁’,‘草长莺飞’,‘车水马龙’,都是很有诗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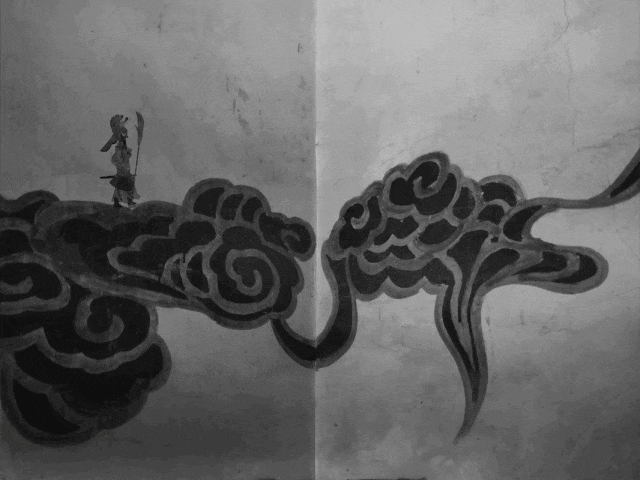
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变迁,逐渐成为他作品关注的核心——在河南北部县城的一个古庙中,严明转身看到院墙角落一个真人大小的无头将军石像。不知道是在疯狂的年代被砸毁,还是被小贩撬去卖了钱,如今只剩一个残像,向人们抱拳拱手。
他举起相机。这张残缺的照片后来成为《大国志》的封面,严明在书中写道,“在我们的文化里,应该没有什么比‘掉脑袋’更要命的事了,曾经的威武和现在的凄绝,在向晚的风雪情境中被推向极度抑郁。最重度的伤残就以这种形式保留下来,别国的维纳斯掉了胳膊仍可以被审美,我们的遗存却这般无厘头了。”
“拍《大国志》里的照片时,其实好多想法已经浮现——比如说这个世界和社会在变迁,有时间的原因,该不该变,会不会有一部分遗憾和代价。那些注视、凝视变化的过程和感伤、怀念的情绪,其实都倾注在画面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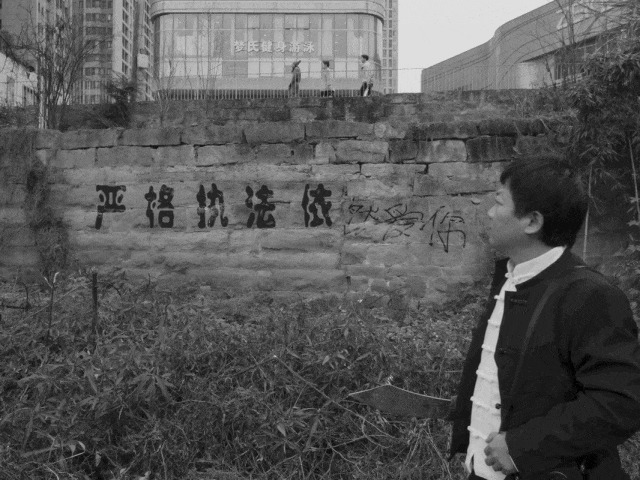

近十年过去,严明又开始探索西北的废墟和遗迹——他找到一些废弃的工厂、家属楼和寺庙,戴上口罩、穿上一双对抗瓦砾和尘土的鞋子,进入“千家万户”: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一楼二楼三楼,“这里的住户或许十几年以前就搬走了,但还是留下了充满视觉互动的遗迹”。
尽管大多地方已经人去楼空,严明还是乐此不疲地通过房间的装修风格和墙上的挂历判断屋主离去的年代;他根据共享的同一套贴纸和海报,猜想楼上楼下几户人家的孩子是好朋友;在一个废弃的水泥厂宿舍,他发现沙发上的花纹是象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又想象它如何陪伴着主人度过年岁,随着主人的离开,这张沙发失去了它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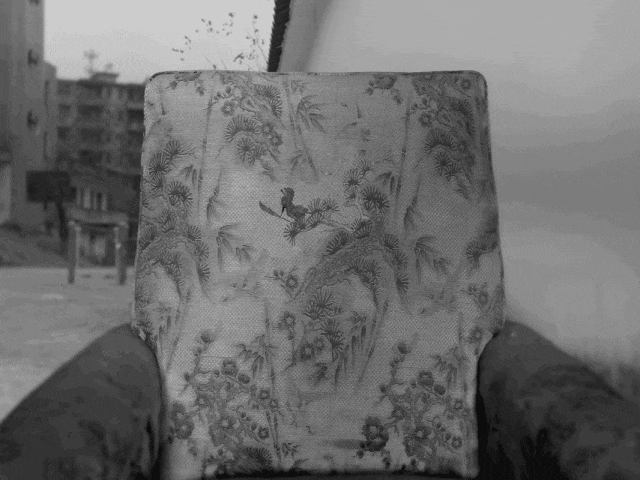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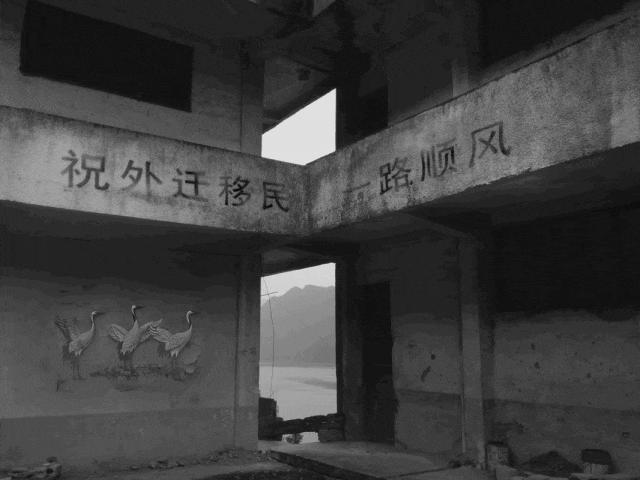
这也让他产生对于观看的思考:人们喜欢废墟探险、喜欢拍老物件,或许是因为时间的叠加作用,“时间是个了不得的东西,你在废墟里走走,遇到墙上泛黄的电影海报,比方说刘晓庆,那是时间和文化的叠加;你捡到一只小孩玩的塑料枪,这是时间和战争的叠加;你看到一个风化的佛像,就是历史、宗教和时间的叠加。不同的生活遗迹跟时间、人生相叠加,就容易产生综合刺激,人的生命那么短,谁对时间没有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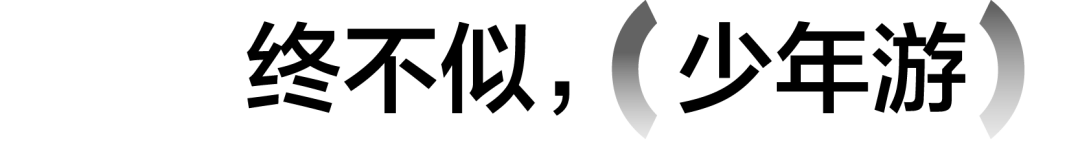
今年是《大国志》出版的十周年。巨变的一面是大国,另一面是小民——书中出现的面孔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过上新的生活;有的已成过客,杳无音讯。严明觉得,摄影大概就是在这当中不断循环:“十几二十年,对任何一个社会或家庭、个人来说,都不只是老去了这么简单,摄影记录的是‘家事’。”
再次回到重庆的朝天门,高楼大厦淡化了江湖气,如同梁山好汉被生活逐一招安。严明想起南宋刘过的那句词:“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每当有类似的感受时,他总会举起相机拍下眼前的一切:
“记录本身是有意义的。一个地方也许会有变迁,但后来者可以通过照片看到它曾经的样子:原来这里有一个亭子,原来这里有个假山。它也是一种留存,总有人会出来提醒你,不要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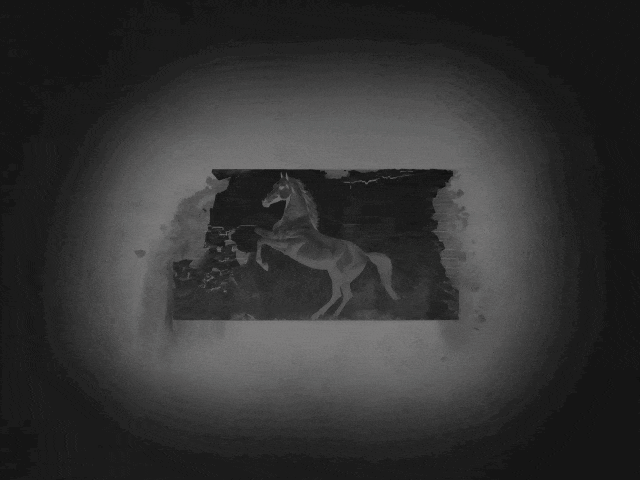

摄影的过程和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严明记得十年前,自己要出发前往一座城市时,往往会带上一本地图册、对照着规划区域内的行走路线、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后来在外面跑的时候,发现有人开始用导航了,前方路口一转就是古代陵墓群”。
紧接着旅游和视频网站出现,打开探险和地理类的长片,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气氛和地貌特征;手机摄影又把摄影的便捷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近些年的不少比赛中担任评委,看到大量的街头摄影、旅游照片,最终胜出的,还是对生活进行的浓缩和提纯。
这也是严明近两年对于摄影的思考:有别于早期对“决定性瞬间”的迷恋、对抓住瞬间和动感的渴望,现在他越来越注重照片中的耐看和情绪感。“外部人士特别容易把摄影和‘抓拍’等同起来,认为拍照就是拍一个瞬间。一张照片也可以成为‘一分钟’的视频,我们要为照片的‘终将静态’作准备。”

唐陵,《大国志》
严明觉得,摄影师还是要不断刷新自己。拍完《大国志》后,他不愿意再重复一本《大国志2》、把自己干成某一种类型的能工巧匠,而是不断在视觉探索上做新的尝试,“在难题面前,我想尝试新的解法。有好多老摄影家不太看重这一点,被老的形式和手法一束缚,很多年就过去了,这是我害怕的。”
害怕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严明曾经反复思考过这个成语:江郎这个人怎么会才尽呢?他是不是原来有个口袋,里面装的都是才,最后像钞票一样一张一张花光了?
后来他觉得,摄影师的“才”是一种持续感动的能力:看到社会中的人和事,还会有反应、产生感动,就是自己再继续去创造、去创作的根本。在此之上,才是新的形式和边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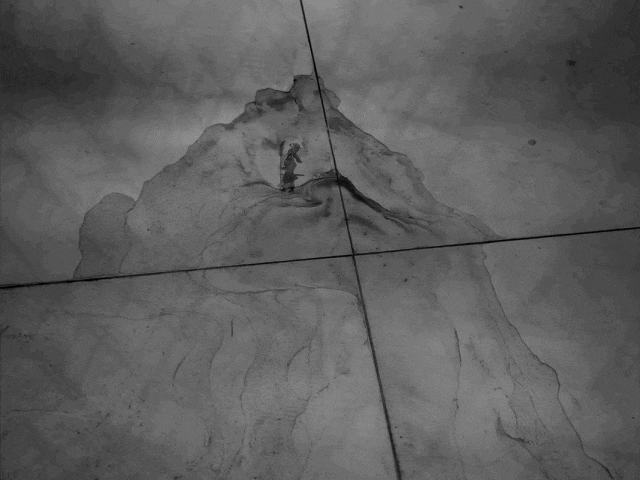
“我当初总结出这句话,就是出于恐惧,我恐惧失去持续感动的能力。我搞摄影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很多人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转行了。”
“我们以前也常讨论,如何不受环境的冲击——如果以后赚钱了、住上别墅了,还会想跑江湖吗?后来才发现这也不是个问题,我到现在也住不上别墅,好在对摄影这个事还是持续热爱。如果你有持续感动的能力,就不会担心它有一天会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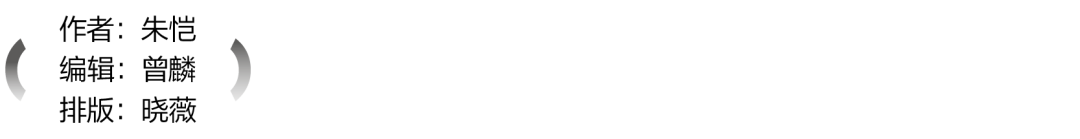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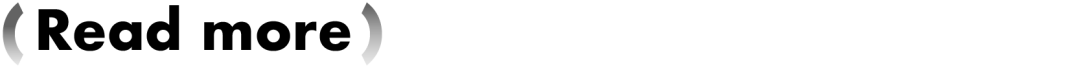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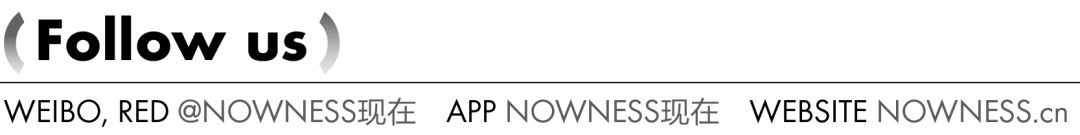
驰盈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